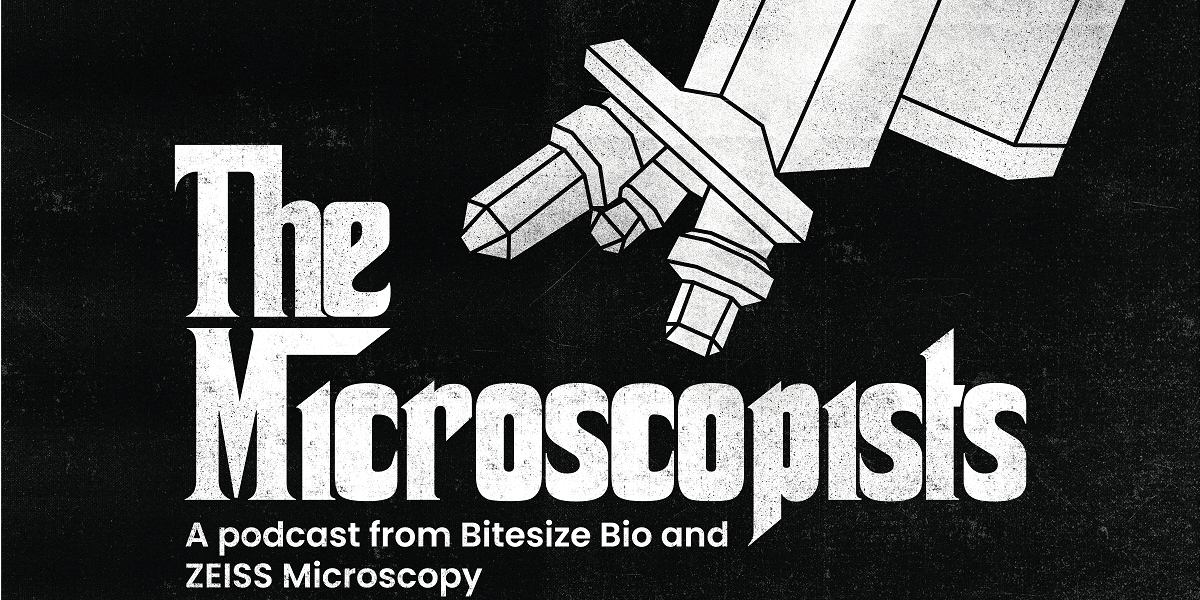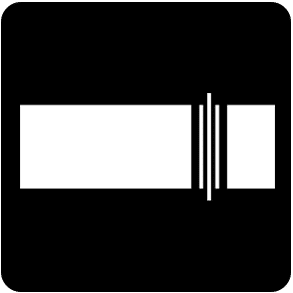大衛活塞(第三)
由
聽現在
看現在

這是自動記錄,可能不是100%準確。
介紹/結尾部分(00:00:02):
歡迎來到的顯微鏡化驗員, bi188bet手机版APPte - esize Bio118宝金博主持彼得奧圖爾由蔡司顯微鏡.今天的《顯微鏡學家》節目。
彼得奧圖爾(00:00:14):
今天的《顯微鏡學家》節目,我的搭檔是戴夫活塞教授兼細胞生物學和生理學係主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在聖路易斯,戴夫使用創新的成像和生化方法來確定糖尿病的新的治療靶點,但顯微鏡和生物學絕對不是他的出發點。和
大衛活塞(00:00:36):
是的,超快激光物理學是我的研究方向。那是我的初戀。
彼得奧圖爾(00:00:41):
直到他對物理學的早期熱情對他來說變得不再那麼有趣。
大衛活塞(00:00:45):
事實上,我想我可能一直想這麼做直到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意識到他必須花兩年時間學習量子力學。我學了一年量子力學,不知怎麼得了個a,但我不明白它的原理。
彼得奧圖爾(00:00:56):
我們還討論了他最近在新加坡的成就,在那裏,他能夠把對旅行和科學的熱愛結合起來
大衛活塞(00:01:03):
它是。我喜歡去那裏,你知道,那裏有12個小時的時差,所以你不會倒時差。這是完全的睡眠剝奪。
彼得奧圖爾(00:01:11):
我們聽說,到目前為止,機緣巧合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衛活塞(00:01:16):
天時地利。我想我開始做的時候我意識到有很多有趣的生物學可以做一旦你有能力做位點定向突變體
彼得奧圖爾(00:01:26):
這一集《顯微鏡學家》都有。你好,我是彼得·奧圖爾約克大學今天和我一起的是來自華盛頓醫學院的Dave活塞。戴夫,你今天好嗎?
大衛活塞(00:01:44):
做的很好。
彼得奧圖爾(00:01:46):
天啊,這是最難的部分。
大衛活塞(00:02:03):
我想是在慕尼黑
彼得奧圖爾(00:02:04):
現在。我想那是一個關於顯微鏡和工作流程的研討會。是的。
大衛活塞(00:02:10):
是的。
彼得奧圖爾(00:02:12):
但有趣的是,我知道你的,你的生物化學,從我的角度,我認為更多的是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方麵,但你的背景是物理,對嗎?
大衛活塞(00:02:21):
是的。因為超快激光物理學是我的事業那是我的初戀。
彼得奧圖爾(00:02:27):
那麼,如果你的初戀不是什麼,那麼誰是你的第二愛呢如果你的初戀是ultra?
大衛活塞(00:02:34):
我的意思是,我當時在研究超快激光和光譜學當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冷戰已經結束了很多固態物理學的資金,尤其是介觀的,以及單一到單一分子類型的固態物理學,還沒有真正發展,正在枯竭。因為很多都是國防相關的資金,我想。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有趣的問題的缺乏,高TC,超導電性還沒有出現。很多有趣的介觀理論比如繪圖和不同的特殊材料都還沒有被開發出來。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在讀研究生。我幫一個叫恩裏科•布蘭頓他最終成為了我的博士導師,他使用激光光譜學,但是把生物分子放在[聽不清]而不是固態物質中。他需要有人可以運行激光器並開發一些新的超高頻並行諧波內容分析工具。這些都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他當時很有錢,我就加入了他的實驗室,然後我就開始做一些你知道的,對生物物理學有點興趣。然後你知道,我決定我要學習一些關於成像的東西因為有,做平行光譜學的想法,不是隻做一個光譜學點,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並行的。我想,你可以快速成像。通過反聚焦,你可以開始做熒光相關,光譜學,很多有趣的分析技術,你可以使用。所以我就去了瓦特韋伯的在康奈爾大學的實驗室,當我出現的時候,兩個光子剛剛被發明Winfried Denk和Jim Strickler,韋伯。他們需要有人了解超快激光光子到秒激光來推動雙光子技術的發展。所以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我想我開始做這個我意識到有很多有趣的生物學可以做一旦你有能力做位點定向突變。位點導向突變蛋白質的起源是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發明的,所以這是一種新的,你可以,你可以拿一種酶你可以對它進行不同的突變。你可以說,讓它不那麼活躍,更活躍,稍微活躍一點不活躍,然後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入口,你可以繪製數據,如果你可以獲得一個入口並繪製數據,物理學家就可以試著弄清楚。所以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慢慢地,肯定地,越來越多地接觸生物主要因為那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意思是,有一些有趣的問題需要研究,我們開始研究它們。現在我覺得我不再是一個物理學家了。現在,我的第二愛是胰髒小孔
彼得奧圖爾(00:05:44):
大衛活塞(00:06:08):
當我10歲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在哪裏讀到過我10歲的時候,我做了我的第一個望遠鏡
彼得奧圖爾(00:06:13):
真的
大衛活塞(00:06:14):
那時,我磨了一個六英寸的反射霓虹燈反射鏡當地的業餘天文團體有這樣的研磨,你自己的鏡子,建立你自己的望遠鏡車間。我把我自己的鏡子接地了用8英寸的管子和小木支架做了一個望遠鏡還有一些你必須從Edmond scientific買的零件,然後做了它。我一直以為我會成為一名天體物理學家。我想那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實上,我想我可能一直想這麼做直到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意識到你必須花兩年時間學習量子力學。我學了一年量子力學,結果得了個a,但我不明白這門課的原理。我是說,我知道怎麼做這些題。我是一個足夠優秀的數學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我大概明白了我喜歡的東西。所以我對它們有一些直覺。 I can, I can, I like things where you can do something to say, here’s a simple version is my theory. Right. And in quantum mechanics, it’s, there’s no such thing.
彼得奧圖爾(00:07:18):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我猜這就是你爸爸的激情被激發的地方,你開始研究物理學,你意識到天體物理學不適合你。
大衛活塞(00:07:26):
是的。
彼得奧圖爾(00:07:27):
在那個年紀,你覺得自己會走向何方?因為簡曆裏肯定沒寫。它是困難的
大衛活塞(00:07:31):
如果他,不,簡曆裏沒寫。這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想做,我真的很感興趣做單摩爾。在一個晶體管中,一個單分子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想法是當你有晶體管時,你知道,很多pn結,很多理論是,體積,但是他們把這些東西做得越來越小這樣你就有100個載流子,或者更少。當你,當你達到那個水平,你就不再,你不再處於統計狀態。你開始進入更多的單分子狀態。所以試著觀察整個重組的軸或者類似的事情,在一個,在一個,在一個材料的連接處你可以得到一些單一的事件。然後,你知道,有沒有可能製造一個晶體管,我想在某種意義上,像量子晶體管在某種意義上現在他們在談論量子計算,在那裏,你真的在看單個,單個的量子事件來存儲數據或處理數據。所以我有點想這麼做,但是我們做光譜學的實驗室沒有,他們在資金上遇到了麻煩。那裏的學生不得不經常做助教。所以對我來說,我喜歡在實驗室工作。 I I’m sort of a, for better term lab rat, you know, I, I like, I like going and turning the lights out and, and giving a Allen wrench in one hand and a mirror adjustment in the other hand and building my own lasers and these sort of things. That’s what I like doing. So
彼得奧圖爾(00:09:07):
告訴我,你不會還在這麼做吧。
大衛活塞(00:09:11):
我後麵不是有個顯微鏡嗎。我,但是不,我,我,我,我,他們不讓我通過那扇門。我的實驗室就在後麵那扇門裏,他們通常不喜歡我回到那裏。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去幫助你,組裝一個新的浮動桌子,光學桌子,讓腿的浮動平衡或類似的東西。但是現在的激光器激光器,我們現在買的是完全密封的腔體,它們沒有用戶可使用的部件。他們通過互聯網接入,如果不能修好,他們會給你寄一個新的,他們會把舊的放在盒子裏,然後把它寄回來,它會告訴你一個故事。當coherence有第一個密封腔時,Ty Sapphire我們有一個,但它不起作用。我想,好吧,我們把上衣脫掉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我想上麵大概有320個扳手和螺絲。我看著這個,我說,320。 I don’t think I can undo all those before their service. Guy’s gonna show up. When I talked to, when I talked to the designers, they said, yeah, I’m sure there was a meeting someplace where, where they said, how many, how many screws do we have to put on before Piston will try to open it? You know, they, so I said, 50, oh no, no, he’ll open 50. So they got to 320 or something. They said, yeah, that’s probably enough.
彼得奧圖爾(00:10:32):
大衛活塞(00:10:34):
是的,我沒有。我,我沒有我已經很久沒有在自己的實驗室工作了。我休過幾次假,2011年夏天在伍茲霍爾實驗室工作,然後2019年在斯達在新加坡。
彼得奧圖爾(00:10:50):
哦。所以你給我發了一張照片,
大衛活塞(00:10:53):
是的,我有。這是,這是我。我在混合緩衝液。我知道。我看起來真的很專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彌補,彌補我的實驗中的緩衝,但是我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實驗,觀察聚合中的阿克頓和鈣細胞和細胞中的鈣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數據,我們得到了一筆撥款。我現在有一個博士後正在研究這個項目,把它向前推進。所以
彼得奧圖爾(00:11:18):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這種想法是一個物理學家拿著Eppendorf Gilson的移液管。
大衛活塞(00:11:26):
我看起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不是嗎,
彼得奧圖爾(00:11:28):
看起來很有說服力。是的。我相信政客們會這麼做。當他們進入護理科學實驗室時,
大衛活塞(00:11:34):
我隻是想做個緩衝。我想,我想應該是其他人向我伸出手。我在他們的實驗室裏沒法用酸堿度計。
彼得奧圖爾(00:11:43):
那麼,你為星之星離開多久了?
大衛活塞(00:11:46):
所以我們,我們,我在那裏。我在實驗室待了八周。
彼得奧圖爾(00:11:52):
你怎麼享受?斯達新加坡。
大衛活塞(00:11:54):
哦,我喜歡,我喜歡我很喜歡去那裏。我在那裏待過很久了。我開始作為合作夥伴去那裏布裏頓的機會大概12、13年前。我想我一直在和Wade Ping Han一起工作,在一個成像成像聯盟。我喜歡去那裏,你知道,要12個小時的時間,距離,所以你不會倒時差。這是完全的睡眠剝奪。
彼得奧圖爾(00:12:59):
一切聽起來很酷。想想這方麵,很明顯我們已經討論過你們的職業生涯是如何發展的,但你們同時也是細胞生物學和生理學部門的負責人,這和管理自己的實驗室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描述。是的。當你開始成為一個部門的領導。那麼,作為係主任,對你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大衛活塞(00:13:24):
對,我想最大的挑戰是,最大的挑戰是與人溝通,讓他們保持一致,讓他們知道你在做什麼。如果你開始做一件事,它會把人們聚集在一起,他們說,是的,讓我們做這件事。然後你就開始做了。如果你不向他們彙報,他們就會認為你沒有做,或者他們認為你做錯了。即使你做的是他們想要的。所以這可能有點違背我的本性。我隻是,是的,我們有這個協議現在我在做我該做的。我要我做完了就去報告。所以這對我來說是,尤其艱難的部分。我認為在新冠肺炎期間管理部門顯然是一個艱難的部分,然後溝通就更重要了,但溝通是如此重要,所以必須要做。 Yeah. Right. I mean, I was the, I was the lifeline for all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bout what was allowed, what wasn’t allowed, how we could keep things going. So it really forced me to communicate that’s that was my full time job really was just communicating up and back and, and side to side, peer to peer with the Dean’s office, to my faculty, with my other chair colleagues across the campus, from the medical school to the arts an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mpuses that were struggling with the same sort of thing. So you know, I think that, that taught me a lot about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that. But that’s certainly, you know,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I’m, I’m good at signing things and, and doing the budget and things like that. I, it just, I’ve always sort of had a knack for, for budgets and numbers. And so that was that just something a lot of chairs really struggle with. And for me, that wasn’t hard. Bu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much more natural communicators and keep people up to date with what they’re doing all the time and that’s not my natural style. So that was that’s, that’s been the hardest, that’s the hardest thing, right? People don’t trust people don’t trust you. It’s like, why wouldn’t you trust me? I’m the most trustworthy guy there is, but, you know, until they’ve seen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 they don’t, they don’t know. So
彼得奧圖爾(00:15:38):
是的。人們,你,你也總是會遇到新的人。所以,那個,那個,那個知識,
大衛活塞(00:15:43):
是的,不,沒錯。
彼得奧圖爾(00:15:44):
新麵孔,你說得對。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一開始就知道?你認為你的管理風格是什麼?
大衛活塞(00:15:54):
嗯,我的意思是,一般來說,我是非常不插手的。我很(聽不清)。我的意思是,我盡量雇傭優秀的人,不妨礙他們。你知道,如果,如果我雇傭了不優秀的人,我必須非常努力地說服他們,他們需要去其他地方。我不會事無巨細地管理他們,也不會一直幫助他們。
彼得奧圖爾(00:16:17):
一場演出有多難,當他們表現不佳時,你怎麼去嚐試,怎麼去表現?你能讓他們最終表現出來嗎?
大衛活塞(00:16:27):
是的。不,一般來說我控製著他們的工資,人們不喜歡減薪
彼得奧圖爾(00:16:36):
那肯定是一場艱難的演出,說,對不起,X,但你
大衛活塞(00:16:42):
我的意思是,你必須記錄下來,你必須記錄下來。我們有足夠的,足夠的管理措施對員工進行年度評估,我們有來自人力資源部門的良好支持,幫助員工提高績效,提供谘詢等等。現在,你知道,對於專業人員,對於小時工,你知道,在我的實驗室,在我的實驗室裏,有幾個人最後獲得了碩士學位。我認為他們完全有能力讀博。我覺得他們需要一個更有經驗的人來幫助他們。事實上,有一個案例,我們讓這個人進入了另一個博士項目。其實他隻是選錯了博士課程。是的。所以回到更多的材料科學,完成了,做得很好。所以我認為,你知道,當人們來到我的實驗室時,我對他們很開放。 This is how I am, and this is, I expect you to be fully self-motivated. And I will, my job is to help you succeed, your job is to succeed. Right. I mean, I, I like, I can’t do that for you.
彼得奧圖爾(00:17:59):
是的。我,我,是的,滿分。我覺得這是一場很難的演出。因為我可以想象,你將帶領這個部門朝著一個方向發展,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想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是的。你知道,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談論的是非常高級的員工,所以你如何讓他們跟隨,還是你就這樣走,就是這樣?
大衛活塞(00:18:18):
好吧,事情就是這樣。我是說,在某種程度上,事情就是這樣的。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人想要改變他們想要更多的支持他們想,哦,我們應該,你們應該做更多這個或更多那個。我說,嗯,那不是,是的。作為一名教職員工我們進行了五年的部門回顧。實際上是6年,因為它應該在新冠病毒開始之前發生,你知道,就在新冠病毒開始的時候,被推遲了。我們有一個外部的訪客來參觀我們的部門並采訪每個人。我們作為教員坐下來製定了一些戰略計劃。 They’re not really so strategic as much as their organizational and tactical, but the idea is what we want to do. And I’ve, I’ve let the faculty lead a lot of those different different things. And some of them go better than others. And, and I think they realize how much work it is to actually make some of these things come, come to, to fruition.
彼得奧圖爾(00:19:23):
所以,所以,我們,我們已經經曆了一個想成為天體物理學家的循環,意識到這不是你要成為物理學家的,意識到機會可能會受到單一粒子材料的限製,然後進入生命科學家的行列,很明顯你仍然保持著,但也承擔著另一種責任。再等10年吧。你理想的工作是什麼?如果你能在世界上做任何工作,你會做什麼?
大衛活塞(00:19:49):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時候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告訴你,如果我退休了。所以我計劃在10到12年後關閉我的實驗室。答:我認為科學是年輕人的遊戲。我認為有太多65歲以上的人有大量的國家衛生研究院資金,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不能很容易地開始。但是我不打算,我關閉我的實驗室,我將退休,不再從事科學研究,但是我,我想我有一個想法,也許寫一兩本教科書,如果仍然有需要的話,現在真的有需要,有一個嚴格的顯微鏡預約。這有點像視頻顯微鏡書的前身和後繼者Shinya井上.有很多東西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但是現在有很多東西是關於我們如何進行分析的,以及如何實現完全數字化無縫的,這些真的需要整合進去。所以這可能是我想做的事。我想做的另一件事是為非營利組織寫網頁。因為我聽說過一些非盈利機構,我想給他們一些錢,我就去他們的網頁。我不知道怎麼捐,我也不會拿起支票本寫出來,把支票裝進信封裏。我隻是不。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信封
彼得奧圖爾(00:21:45):
啊,那很酷
大衛活塞(00:21:47):
也許隻是為了恢複我的編程技能,因為我教我女兒Java編程,所以我意識到我有多想念做那種事情。
彼得奧圖爾(00:22:02):
所以,很明顯,在實驗室裏有很多壓力。你在實驗室之外都做些什麼來放鬆?
大衛活塞(00:22:11):
我現在有幾個女兒在上高中,我主要做的就是想知道她們在哪裏,她們是否需要搭車或其他東西。我的大女兒現在開車。那麼,
彼得奧圖爾(00:22:24):
你的家人呢?
大衛活塞(00:22:25):
這是這是這是我的家人。是的。沒關係。是的。我們去新加坡和阿斯達的原因之一是我想讓我的家人離開這個國家,我想我的女兒們當時大概12歲,12歲和10歲。差不多吧,13 13 11。新加坡人說英語,對吧?所有的標誌都是用英語寫的,即使他們說中文或印度語,所有的標誌都是用英語寫的,你可以用英語出行。所以我們有機會去了吳哥窟。這是我們在吳哥窟,那是我遺願清單上的一個地方。 That’s my wife there in the paint on the, on the, on the right, I guess. Yep. and and obviously the old bald guys, me and my older daughter, Casey is on the right. And then Elena is the one is on the left. So we had, we had a blast in, in at angkor wat and that so that’s, that’s yeah, we, I mean, we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travel. We don’t, we don’t get to travel as much as we used to. We go to Florida for a couple of weeks for vacation and go to the beach. And the girls are both having friends down this year to, to stay in the house with us. So we’ll see how, we’ll see how that goes.
彼得奧圖爾(00:23:51):
他們在物理學或生命科學方麵是否追隨了你的腳步?
大衛活塞(00:23:55):
不,一點也不。我認為我的大女兒更喜歡英語。我想她可能想做寫作,雖然她現在想當醫生。所以我認為這與她的朋友有更多的關係。媽媽是兒科醫生,但她在考慮讀醫學預科。小女兒非常非常喜歡數學和科學,但我認為她根本不想成為一名專業科學家。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想過她到底喜歡寫什麼。她寫了很多有創意的文章,寫了很多故事,還讀了很多書。所以
彼得奧圖爾(00:24:34):
大衛活塞(00:24:39):
是的,這是正確的。好吧,希望在我的,我的,我的行業裏,我們沒有太多的創意寫作。
彼得奧圖爾(00:24:44):
大衛活塞(00:24:46):
我們閱讀,我們在評論文章的時候偶爾會讀一點,
彼得奧圖爾(00:24:51):
你還發了一張這個的照片,但你抓到了。
大衛活塞(00:24:57):
是的。這是一條36磅重的條紋鱸魚,是我從伍茲霍爾發現的。這是另一件事這實際上代表了我的教學。所以,你知道,我在伍茲霍爾在芒特霍利奧克學院,生物實驗室,顯微鏡課程,我在伍茲霍爾學院教授AQLM和OMIBS,然後是春季和秋季課程。然後我和西蒙·沃特金斯一起教書。這門課,我們在緬因州開了20年。我想20年對我來說足夠了。但是這是,是的,我們去了,我們一大早就去了,在十月的時候,我們隻是開著一艘小船。天氣很糟糕,但我的朋友們說,如果不是糟糕的天氣,你永遠也抓不到這樣的東西
彼得奧圖爾(00:25:44):
對於不熟悉伍茲霍爾球場的同學,請繼續,簡單介紹一下。
大衛活塞(00:25:49):
哦,所以伍茲霍爾的海洋生物實驗室是一個古老的海洋實驗室。如果你在英國,你知道工商管理碩士可能在普利茅斯,它基本上是模仿普利茅斯MBA的模式。這是他們捕撈魷魚的另一個地方魷魚巨頭埃克森公司就在那裏。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那裏對它們進行貼片記錄當他們對海膽海星和其他東西進行胚胎學研究時。那是在聯邦快遞出現之前的時代,你不能把東西送到你的實驗室。你必須去,去樣本所在的地方。伍茲霍爾大學有一個大型的暑期項目,他們教授生理學課程和神經生物學課程,這兩個課程都是世界著名的。但是他們也有專門的課程。我還要上顯微鏡課。多年來,作為一家大型顯微鏡公司,鮑勃·艾倫以及井上伸彌(Shinya Inoue)都在那裏授課。Shinya在那裏工作了很多很多年算是圖像的負責人。大概有20到30個人來,10天或8天,我不知道以前是10天。我想現在大概有八天的科學營了。基本上早上8點開始,晚上10點結束早上上課下午上實驗室,下午晚些時候上課,晚上再上實驗室。最後你回家再睡一會兒
彼得奧圖爾(00:27:18):
戴夫在想井上的書,視頻麥克風是視頻顯微鏡。這不是視頻顯微鏡嗎,
大衛活塞(00:27:25):
是的。視頻顯微鏡,
彼得奧圖爾(00:27:27):
就像聖經一樣。你說過,當你退休的時候,你可能會寫或更新類似的書,你認為在今天的時代是這樣嗎?不是,不是在文本上,不是,不是在後麵,但是你認為,你認為這個領域現在變得這麼大了嗎?
大衛活塞(00:27:43):
噢,是的。它肯定不會像最初寫的那樣是百科全書式的,但即使是他寫的第二個版本肯春天第二版就沒有那麼百科全書了。它最後有更多定量的東西,但我認為,什麼,什麼不是真正的定量,對吧?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就是不再拍照了。我們取數據。如果你用的是共焦相機,CCD或無縫相機,你現在正在采集數據,你可能沒有在采集數據,因為你沒有注意。所以你隻是在拍照,但你有能力用很少的額外工作來獲取數據,但你必須理解你在做什麼,你必須理解。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顯微鏡來定量,是你想要做的。然後討論如何處理這些數據,不把它搞砸。我的意思是,基本上顯微鏡下的東西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對吧? You can only make it worse after that. Right. What comes out of the objective lens is the best you can get and everything else just makes it worse. So the trick is to talk about how to make it as little worse as possible. And so I think that it really, it’s more about how to do microscopy in a way that teaches people how to do microscopy, not every kind of microscopy you could ever do. And there’s a lot of books that have that, right. There’s a lightsheet book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ways to do lightsheet. And, and there was a lightsheet conference that we阿布·庫馬爾而且加裏Laevsky剛剛在伍茲霍爾舉行。我是第一次回到伍茲霍爾球場,自從我,呃,不是自從我釣到那條魚之後,但到今年已經10年了,我可以告訴你,科德角沒什麼變化。但無論如何,有一個人,我不記得是誰了,他做了一個演講,他們有在文獻中找到的所有縮寫。它填滿了一整張幻燈片光片顯微鏡的縮寫不同的東西。正確的。所以你不想成為那樣的人。我的意思是,關鍵是lightsheet給了你一種獲取三維數據的方法。共焦也是一樣,對吧?那麼對我來說,草皮,草皮共焦,光板都是一樣的嗎?有一點關於,有一點關於擴散是什麼厚度和這些東西,但這些都是微妙的,對吧? I mean, that’s, the data comes out in some sort that you get some sort of line of data that has some signal to background that has some signal to noise, and you can deal with that. Right. And those are the same, right. What comes out of an image is the same. And so what resolution is within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well defined, but people think of resolution as being oh, the, the light, sheet’s two microns thick, but that’s not your resolution. Right.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I read that resolution is different and confocal than a widefield which is just not true. Most of the time, if people use a one area unit pinhole or bigger, the resolution’s the same, the 3d discrimination is much, much different.
彼得奧圖爾(00:30:50):
是的。因為專注,所以你可以實現。
大衛活塞(00:30:53):
是的。但是決心是有意義的,對吧。你不能隻是,所以我認為隻是教人們這些詞的意思,它們的意思和為什麼,為什麼它們是這個意思。這意味著你一開始可以從你的圖像中收集到什麼信息,並在你處理它的時候保留在你的圖像中,這很重要。
彼得奧圖爾(00:31:10):
所以思考成像數據和成像數據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它,它是定義上的。是的。大數據。並且,根據您使用的模式,數據大小與之成正比。你如何看待不僅僅是量化和保存數據,你如何看待數據分析的複雜性以及如何從移動的數據中獲得最大的收益
大衛活塞(00:31:33):
未來?是的。這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一件事。我們從貝克曼基金會獲得了光片顯微鏡的資助,主要是為了研究這些東西。很明顯,你可以用壓縮做一些事情,用無損壓縮,但這些都不能讓你走得很遠。我們有我們的,我們有一個雙視角的燈罩和大相機。我們用來做高光譜成像。有了它,我們可以做的是,我想是每秒2.8 g。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一個實驗中完成10tb的數據。這是不可能的,它,它,我的意思是,除了拿著那10tb的光盤拿在手裏,把它移動到不同的地方,你什麼也做不了。 The internet isn’t fast enough, nor will it ever no, will it be fast enough? But what we, what we have is we have a lot of data that is useless in there, right? We might be finding, we might be tracking particles. We might be checking cells, but we have all the area around ourselves in plaque. We have all the area, the cells that aren’t there. So we need to figure out ways to reduce those data sets only to the cell we’re looking at in real time because just, you know, you might wanna keep those 10 terabyte discs around forever, but you’re never gonna be able to analyze it, get it, move it around and deal with it. Even using things like highly efficient programming languages, like Julia that are all real time and they don’t load everything into Ram. And they, they do memory swapping without you knowing it and allow you to, to work. And apparently in real time on big data sets, but, you know, 10 terabytes is still too big of a data set. And so you wanna do things that are correlations across time and correlations across space, but you need to just throw away all the data that isn’t there. Right? So if you’re, if you have 16 bits, every place you have, or 32 bits, every place you have dark black, you know, sure. There’s some fluctuations there, but you don’t care. It’s not tied to cell. So, so we have,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that just shrink the dataset into 20%, just easily, just by throwing away data. You don’t have that isn’t data and mapping things. And so there’s a lot of idea about doing holographic maps. Yep. So you can, you can reduce things with holographic maps, into lossless data sets that keep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they keep the data information in really deep you know, really deep bit numbers that reflect larger data sets. Uh and so tho those sort of things I think we’re gonna have to do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with this, right. So if we can take that 10, 10 terabytes and shrink it down into a couple hundred megabyte, a couple hundred gigabytes, well, then we can move it around on the internet that we have. Now we can process it on the GPU clusters that we have sitting on our desk and we can start to visualize it. We need to visualize it in real time. I mean, machine learning can visualize it in real time and track particles and do what, but we still have to look at it ourselves and see things that we aren’t even asking the machine to see.
彼得奧圖爾(00:34:40):
是的,不,絕對。你會說,我,我隻是在想,回到我開始用液氮冷卻CCD相機成像的時候,我相信你記得那些日子,倒它,冷卻它,是的。最終的尺寸是最小的,但與我們現有的相比是巨大的,你是否認為現在用顯微鏡觀察它比20年前更難還是認為它更,我不知道答案。
大衛活塞(00:35:11):
不,實際上,這樣更容易。我認為,我的意思是,我認為你可以用10萬美元買到高端的房子。你可以買一個相當高端的顯微鏡,你可以有足夠高的足夠高端的東西,真的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你可以捕捉各種各樣的東西。我的意思是,我看到人們基本上隻是在捕捉噪音。他們太敏感。正確的。它們隻是捕捉噪音,隻是放大噪音。和
彼得奧圖爾(00:35:42):
是啊,也許這才是重點。也許是也許我們,我,我,我們從來沒有問過簡單的問題。你知道,我們一直在突破它的極限,但也許我們不會惹上那麼多麻煩,因為它不是現成的。
大衛活塞(00:35:54):
它不是交鑰匙。所以去那裏的人都知道你必須知道你要做什麼,要做什麼。你必須投入時間。正確的。如果你要花時間在這上麵就像以前的電子顯微鏡一樣,你必須自己把柱排成直線,做所有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沒有人不能立即看到一個EM然後知道它是好是壞,你知道,看,隻看一張圖片然後說,哦,這個,這個樣本不好。這就像,你怎麼能,你知道,你怎麼能說,他們就是知道,對吧?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進去說,哦,這是模糊的。我甚至不能告訴你哪個方向是模糊的。那個人說,我不知道怎麼聚焦。 Like, what do you,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Well, how do you know that? It’s
彼得奧圖爾(00:36:34):
現在看起來如何,
大衛活塞(00:36:35):
當你看到它被打破的次數足夠多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這個,對吧。但現在他們還沒有崩潰。它們有完美的對焦能力,還能自動對焦。隻有一次,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正確的。
彼得奧圖爾(00:36:46):
這周沒有一個會議有數據集,我們看看,然後轟擊問題,這看起來不太對。
大衛活塞(00:37:04):
是的。
彼得奧圖爾(00:37:06):
所以樣本發生了什麼,那就是,是的。這隻是一種參與度。我認為如果你是對的,你產生了大量的數據和他們的圖像,但人們需要兩者都看。是的。他們需要設置數據
大衛活塞(00:37:21):
但他們沒有。是的。所以它們拿走了它們的細胞,不管怎樣。他們製造了一個含有綠色熒光蛋白的轉基因動物。他們把它帶到顯微鏡核心,他們每小時支付50美元來使用某種高端顯微鏡和其他東西。然後他們回去試著在他們的筆記本電腦上分析,沒有內存,沒有計算能力。他們不會在這方麵投資,
彼得奧圖爾(00:37:47):
失去工作。對我來說,它會回到,所以我有一些關鍵的問題,我真的很想有一個感覺,但我要先問一些快速的問題。PC或Mac
大衛活塞(00:37:58):
電腦。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隻是所有的儀器都是由電腦控製的
彼得奧圖爾(00:38:05):
麥當勞或漢堡王
大衛活塞(00:38:06):
既不。
彼得奧圖爾(00:38:08):
那你的外賣選擇是什麼?
大衛活塞(00:38:11):
我在家做飯。如果那是我要做的事情。啊,
彼得奧圖爾(00:38:14):
你喜歡做飯還是洗碗?
大衛活塞(00:38:17):
哦,我這兩個。實際上。我,我兩者都做。我,我,我,我做飯,我在家做飯我洗鍋,因為我不能忍受別人洗我的褲子。
彼得奧圖爾(00:38:29):
啊,很有趣。你洗你的褲子,但其他東西都要放進洗碗機。
大衛活塞(00:38:32):
是的。或者,或者其他人來處理。是的。
彼得奧圖爾(00:38:34):
是的。但你可以待在洗碗機,因為它們是平底鍋。
大衛活塞(00:38:38):
這是正確的。有時候我得把它們從洗碗機裏救出來。
彼得奧圖爾(00:38:41):
大衛活塞(00:38:46):
隻是一切。是的。但主要是油炸。我的意思是,我有鑄鐵的,還有一些染色的,還有一些不鏽鋼的,還有
彼得奧圖爾(00:38:55):
我從來沒問過別人,你有幾隻煎鍋?
大衛活塞(00:38:59):
我想我用了三個。
彼得奧圖爾(00:39:04):
這點我贏過你了。
大衛活塞(00:39:10):
我有很多,我有很多,但我不用,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可麗餅鍋。我隻是不。我每年做一次可麗餅。所以我不會說我用它。
彼得奧圖爾(00:39:19):
是的。我想我大概有7個,但是有有3到4個硬核的被使用。
大衛活塞(00:39:24):
是的。
彼得奧圖爾(00:39:25):
對於非常特定的項目或體積。是的。大家庭。所以長大。是的。茶或咖啡。
大衛活塞(00:39:32):
哦,咖啡,
彼得奧圖爾(00:39:34):
葡萄酒或啤酒嗎?
大衛活塞(00:39:36):
酒,
彼得奧圖爾(00:39:38):
巧克力和奶酪。
大衛活塞(00:39:41):
我想,這取決於它取決於什麼
彼得奧圖爾(00:39:50):
好的。你是黑巧克力愛好者或者牛奶巧克力愛好者。
大衛活塞(00:39:54):
不再有黑暗,
彼得奧圖爾(00:39:55):
更黑了。我並沒有問你要喝什麼咖啡?美式咖啡嗎?這是牛奶嗎?這是咖啡嗎?
彼得奧圖爾(00:40:03):
你有一個大名單。
大衛活塞(00:40:04):
是的。嗯,實際上我喝濃縮咖啡,如果我喝濃縮咖啡,我大概要喝50杯。因為我是個喜歡量的人。所以一般來說,這是稀釋的濃縮咖啡。
彼得奧圖爾(00:40:16):
你絕對不應該稀釋濃縮咖啡。這是不,
大衛活塞(00:40:18):
它很長,我們這麼說吧。它很長,
彼得奧圖爾(00:40:22):
大衛活塞(00:40:26):
我更像是一個夜貓子,但我的工作更像是早起的鳥兒。
彼得奧圖爾(00:40:30):
好的。你的食物天堂是什麼?你最喜歡什麼食物?
大衛活塞(00:40:35):
我最喜歡的食物類型。我是說,從遺傳學上講,我是意大利人。所以我認為是意大利語。
彼得奧圖爾(00:40:42):
好的。那你最不喜歡的呢?如果你要去參加一個會議或者有人帶你出去吃晚餐,當你邀請了一位演講者,他們會帶你回去吃晚餐這是一份固定的菜單。你害怕他們會把什麼擺在你麵前?
大衛活塞(00:40:54):
哦,青豆。
彼得奧圖爾(00:40:57):
這是另一個。
大衛活塞(00:41:02):
我喜歡所有的食物。我都很喜歡
彼得奧圖爾(00:41:07):
習慣。你有什麼壞習慣嗎?
彼得奧圖爾(00:41:11):
除了你和穀歌相處時不交流
大衛活塞(00:41:14):
彼得奧圖爾(00:41:22):
順便問一下,那是紅葡萄酒還是白葡萄酒?對不起。
大衛活塞(00:41:24):
是的。通過各種方法
彼得奧圖爾(00:41:40):
好的。
大衛活塞(00:41:41):
我認為這是一種象征,但是我,我在吃飯的時候喝酒。如果我吃清淡的食物,或者我們會吃很多魚,所以我們會喝更多白葡萄酒。但
彼得奧圖爾(00:41:53):
好的。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讓你討厭的東西嗎?
大衛活塞(00:41:57):
噢,是的。人們碰我的東西。
彼得奧圖爾(00:41:59):
是放在你家裏的桌子上還是
大衛活塞(00:42:02):
不管他們搬到哪裏,都不會放回去,對吧。
彼得奧圖爾(00:42:11):
哦,我認識一個人,隻要移動他們車上的東西就很容易,就像移動他們所在的地方。
大衛活塞(00:42:16):
嗯,你知道,我的,我的洗發水在浴室的角落裏,它在一個特定的角度,所以我可以伸手把它泵到我的手上,我的妻子清潔它,並移動它。就像,我把它泵得滿地都是。因為我,我是說,每年的這個時候,太陽都升起來了,但在冬天,我從不開燈。我,我在不開燈的情況下進去刮胡子洗澡,我是一個光譜學家。正確的。所以
彼得奧圖爾(00:42:38):
大衛活塞(00:42:40):
我,我,你知道,我在災難性的黑暗中工作了三年,做了一個職位,所以
彼得奧圖爾(00:42:45):
好的。我可以理解。你隻是在想送禮會嗎?我們有不同的洗發水和沐浴露之類的。我們兩個都在用它。而我,我喜歡一切都朝著正確的方向。所有的東西都是按身高順序排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是的。臉朝上,轉錯方向。 It’s like,
大衛活塞(00:42:58):
是的。我是說,我不在乎她怎麼處理她的。你可以把它放在她想要的任何地方,但是
彼得奧圖爾(00:43:03):
不,不,你不能就這麼倒下。必須是麵圓的。它必須看起來整潔。整潔。
大衛活塞(00:43:08):
我不在乎它看起來怎麼樣。我隻需要能夠擊中它,讓它進入我的手。
彼得奧圖爾(00:43:12):
大衛活塞(00:43:13):
她大概有10度,你知道,大概10度
彼得奧圖爾(00:43:17):
寬容
大衛活塞(00:43:17):
鏡子在那裏。這是可能的。仍然
彼得奧圖爾(00:43:21):
書或電視。
大衛活塞(00:43:22):
那是什麼
彼得奧圖爾(00:43:23):
書或電視嗎?
大衛活塞(00:43:25):
什麼?什麼是
彼得奧圖爾(00:43:26):
電視。你喜歡什麼?對不起。我還是笑了。哦,你,你為什麼不喜歡看書或看電視呢?
大衛活塞(00:43:30):
好吧,我,我看電視。我喜歡看電視上的體育節目。所以有時候我會一邊看書一邊做。
彼得奧圖爾(00:43:38):
好的。我,我,你把這個發給我。所以看你,
大衛活塞(00:43:43):
噢,是的。這是因為我在聖路易斯,對吧?這是聖路易斯紅雀隊。我們每年都去看紅雀隊的比賽,我和妻子去看紅雀隊的比賽,他們對陣舊金山巨人隊,那是我小時候的家鄉球隊。所以我們相處得很好。有一年我過生日,我們買了好票。去了那裏
彼得奧圖爾(00:44:02):
你完全準備好了。然後你拿到了帽子的頂部
大衛活塞(00:44:06):
噢,是的。是的。我是說,這是,為什麼不呢?我是說,這是,這是棒球之城,對吧?所以你,你不想,你不想成為唯一一個不戴正確的帽子和球衣出現在比賽中的人。
彼得奧圖爾(00:44:18):
那你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
大衛活塞(00:44:24):
我最喜歡的電影,一直以來我最喜歡的電影可能仍然是《星球大戰》。盡管我會告訴大家要麼是《綠野仙蹤》要麼是《脊椎穿刺》
彼得奧圖爾(00:44:34):
你為什麼這麼做?
大衛活塞(00:44:36):
嗯,因為,因為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那些電影是最好的電影,但我最喜歡的電影仍然是星球大戰,因為我是在我15歲的時候看的,它上映了,我們以前從未看過。和
彼得奧圖爾(00:44:54):
你知道的,
大衛活塞(00:44:55):
所以,
彼得奧圖爾(00:44:56):
不,這可能是我聽過的最好的理由了。為什麼你不是星際迷,假設你是星球大戰迷,而不是星際迷航迷。
大衛活塞(00:45:02):
我以前喜歡看《星際迷航》我是說,但對我來說,星際迷航在1969年就結束了。沒有別的星際迷航了
彼得奧圖爾(00:45:11):
啊,選擇困難。哦,下一代。
大衛活塞(00:45:15):
那是什麼?
彼得奧圖爾(00:45:17):
哦,隻是,哦,
大衛活塞(00:45:18):
我們有《星際迷航》。我們為什麼要看?我隻是不喜歡,我是說,我們有星際迷航。你可以有另一場演出,叫別的名字。
彼得奧圖爾(00:45:24):
大衛活塞(00:45:25):
又不是《星際迷航》
彼得奧圖爾(00:45:27):
所以我仍然喜歡皮卡德[聽不清]皮卡德也是。超級粉絲。你最喜歡的聖誕電影是什麼?
大衛活塞(00:45:38):
最喜歡的聖誕電影。我猜不是查理·布朗就是格林奇。我的意思是,他們,他們我每年都看這兩部電影,所以我有這兩部電影的DVD。
彼得奧圖爾(00:45:52):
好的。
大衛活塞(00:45:53):
我兩部都看。
彼得奧圖爾(00:45:55):
德魯,這是我們家的事嗎?你們一起看的嗎?
大衛活塞(00:45:57):
我讓每個人都看。是的。
彼得奧圖爾(00:45:59):
你做的一切。看。好悲傷。我們有家庭電影嗎,爸爸,我們離聖誕節就這麼近了。我們現在就得看著他們。我們現在就得看著他們。
大衛活塞(00:46:08):
我從來沒有如果爸爸想看,沒人想每隔一段時間就看一次他們發現了一些東西就像我的小女兒發現了歌曲殺手皇後所以我拿出我的舊LP給她播放。
彼得奧圖爾(00:46:26):
然後她就不喜歡了。
大衛活塞(00:46:28):
不,不,她還是喜歡。她還是很喜歡,但如果我告訴她,她就不會喜歡了。
彼得奧圖爾(00:46:33):
是的。它的訣竅。不是嗎。確保他們確信這是他們自己的決定。這就是他們喜歡的。這是一種管理技能。讓人們認為這是他們的主意。
大衛活塞(00:46:41):
這是他們的想法。是的。
彼得奧圖爾(00:46:43):
讓我們繼續往下說,那些更喜歡的人,你有沒有因為什麼原因最喜歡的出版物?最難忘的,最喜歡的還是最難忘的?
大衛活塞(00:46:56):
我想我最喜歡的是自然方法,我們寫的GFP文章邁克•戴維森.我的意思是,在它出版的時候,邁克已經去世了,但是它有絕對的,你知道,它有每一種漂白劑漂白每一種漂白劑,表達和亮度為每一個綠色熒光蛋白那是當時可用的。這仍然是,你知道,這是這是一場在很多方麵都很強迫的旅行,但這一切都是正確的。嚴格。當你看到一個新的綠色熒光蛋白出來,你看著他們的測量結果,這是很難的,我對他們一點信心都沒有。你可以比較一下,把我們得到的信息和文獻中報道的進行比較。有些人做得很好,有些人做得很馬虎。這是由四五個不同的人在兩個不同的實驗室裏完成的。所以總是有大量的數據。那是,我的意思是,有,我仍然有所有的數據,它在40,我想42 tb的磁盤上,很多。
彼得奧圖爾(00:48:07):
好悲傷。那是很多的日期。這對我們和蛋白質來說是很多的,但這仍然是大量的數據。
大衛活塞(00:48:12):
是的。嗯,我有所有的,它有所有的圖像,所有的原始圖像,所有的照片,漂白,有寬視場的細胞,旋轉圓盤和共聚焦,激光掃描共聚焦。
彼得奧圖爾(00:48:22):
是的。我們談到了量化和數據的重要性。實際上,我,我這幾乎是令人震驚的,因為我,你知道,我過去也設計過類似的實驗,但實際上這充滿了挑戰、困難、正常化和其他一切。我不得不說,解決了這些問題是一項相當大的成就。是的。並找到了解決方法。事實並非如此,它在紙上聽起來和看起來都很瑣碎。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大衛活塞(00:48:50):
是的,不,不,我同意。我同意。事實上,它在很多方麵都是很直接的,但是它很難得到,很難得到細節。正確的。我知道,當綠色熒光蛋白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我說,哦,我們,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測量量子效率,亮度,消光和照片漂白。如果photo有一點photo轉換,在原始的兩種狀態之間。我們想看看,他們是否知道,如果他們用紫外線照射它,他們可以使它更吸收藍色。但我們也發現,如果你擊中藍色,你也可以讓它更吸收藍色。我們想要降低這兩個,這兩個的量子產量,我們發表了這個,每個人都像,哦,我想,肯定每個人都會做這個。所有人都說,哦,大衛。 So I’m glad. So, so glad that you did this. So I thought everyone would be doing this.
彼得奧圖爾(00:49:41):
那是你最喜歡的出版物?那你最喜歡的顯微鏡技術呢?你有嗎?
大衛活塞(00:49:47):
好吧,我想我是有意的,我沒有,但它應該是某種燈罩。
彼得奧圖爾(00:49:57):
好的。
大衛活塞(00:49:57):
我的意思是,真的是薄板
彼得奧圖爾(00:49:58):
方法技術。隻是
大衛活塞(00:49:59):
光。是的。光片,獲勝的技術,對。因為它在低期望強度方麵給了你所有的優勢。所以降低照片漂白基因更溫和的優點,你知道的,3d S空間的空間辨別。所以,
彼得奧圖爾(00:50:20):
所以我想問一些輕鬆的問題,你職業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光是什麼時候?
大衛活塞(00:50:29):
哦,博士後。毫無疑問。
彼得奧圖爾(00:50:31):
是的。
大衛活塞(00:50:32):
是的。我在瓦特·韋伯的實驗室。我們有很多資源。兩個人剛剛被發明出來。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研究它的人,因為Winfried Denk去了IBM研究鑽石近場掃描。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了一些聰明的生物學家過來和我們合作,是的,我就在早上10點進入實驗室打開激光一直工作到深夜關掉激光,然後回家吃晚飯。有些人有時會有人和我一起做實驗,有時我自己做。和
彼得奧圖爾(00:51:12):
你是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的呢?因為很明顯樣本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你是如何應對不同的生物學和樣本的呈現方式的?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你是如何適應這種情況的?
大衛活塞(00:51:26):
我的意思是,我們能做的不多,對吧。我們還沒有Ty Sapphire,所以我們真的被困住了GFP還沒有被發明出來,還沒有被克隆出來。所以我們真的被鈣指標困住了。我們做了大量的NADH和FAD自動熒光。很明顯,NADH是我們做的一件大事,有點像開創了韋伯的實驗室在他實驗室的一些人身上經常使用它來做神經方麵的研究,我們在眼窩和肌肉上也經常使用它。我們仍然把它作為一種,作為一種標準的標準技術在我的實驗室裏,還有黃素。所以我們用了很多自動熒光所以基本上,如果人們想要活細胞,他們需要自己製造。所以約翰萊德爾他當時正在研究心肌細胞,想出了一個博士後這是在iacotes出現之前的時代。所以他們隻是訂購,他們訂購動物,可能把它們帶來,或者訂購它們,在康奈爾大學把它們帶走,取出心髒,在那裏分離心肌細胞。我們讓他們在舞台上表演,我們工作了一整晚,直到我們退休,然後第二天早上早起,去吃早餐,然後回來繼續工作。你知道,在一天結束的時候,我回到家,然後在早上,當事情還在預熱的時候,我回來分析數據。就是這樣。沒有書麵文件。每隔一段時間,你要去參加一個會議,你必須填寫旅行表格,但那三年除了寫論文什麼都沒有,你知道,就是收集數據,分析數據,寫論文。
彼得奧圖爾(00:53:07):
是的。所以那個時候,我想,
大衛活塞(00:53:11):
另一件事是,博士後的時候,我有四五個不同的項目,但作為研究生,它們不一定是相關的。你不能研究的東西不會寫進你的論文。好吧,我想你可以,但它幫不了你太多。對吧?是的。就像我常說的,我叫它研究生院是有原因的,因為我想畢業
彼得奧圖爾(00:53:31):
大衛活塞(00:53:40):
我的意思是,並不是說我,從物理轉到生物而且我從來沒有在有RO的實驗室工作過,RO是NIH的主要資助機製這真的很困難。雖然我得到了係裏的很多支持我們發表了一些論文,顯然雙光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在我們得到一些生物學結果之前,很難獲得資助。正確的。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當時的壓力應該比現在大得多,但我當時竭盡全力,盡我所能。事實證明這可能是在做正確的事情,我的意思是,顯然,我認為COVID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精神上的折磨。你知道,這與當時美國的政治形勢相吻合,這也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彼得奧圖爾(00:54:38):
是的。不同的壓力。也許和其他環境相比。我有一個問題現在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你最喜歡的會議是什麼?
大衛活塞(00:54:46):
我最喜歡,嗯,我去生物物理協會這是我作為研究生參加的第一次會議,那是1986年。哦,那是總統們。是的。所以這就是Taekjip哈後排坐在我旁邊的人會問,即將上任的總統是嗎蓋爾·羅伯遜在前麵右邊。有卷曲的白頭發,總統現在和凱茜羅耶在我之前是總統嗎弗朗西斯Seperovic就在你的上麵,你是我之後的主席[聽不清]在凱茜之前的兩個主席之前盧卡斯都要麼介於兩者之間,要麼是最後兩種。這是你們知道的,連續7位生物物理學會主席。
彼得奧圖爾(00:55:31):
那個社會對你來說有多重要?它扮演著什麼角色,如此重要?
大衛活塞(00:55:36):
我認為,對我來說,生物物理學對我來說,生物物理學是我學習的地方我在那裏遇到了生物學家我在那裏遇到了生物學家,他們想要量化,我在那裏遇到了生物學家,他們有樣本可以用在最新最好的技術上。所以,這是一個會議,它吸引了很多工具構建者。就像我在研究生院或博士後的時候,和那些真正的高端用戶,那些技術的高級用戶,那種更傾向於定量的生物學家。顯然,電生理學在那裏非常重要。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單分子的在那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認為,對我來說,我去那裏,我看到人們正在建造的最新最好的工具,並思考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實驗中使用什麼。所以我變成了,可能是技術的高級用戶,而不是開發人員。
彼得奧圖爾(00:56:44):
當然,我想它也能讓你旅行。因為你說,我記得你之前說過旅行是
大衛活塞(00:56:50):
好。是的,但是我的意思是生物物理學會議,當然,我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事實上,這次會議,今年是2022年在舊金山,是我們兩年來的第一次會議。你知道,那是我第一次開會,我永遠是一個平民。所以我大概在2000年左右加入了生物物理學雜誌的編委會,從那時起,我參與了不同的事情,所以大約20年裏,我一直在忙著達到頂峰,並在2019年擔任總裁。如果你是會議的主席,你周五出席周四離開,在這期間你的日程排得滿滿的
彼得奧圖爾(00:57:43):
然後是麵對麵交流的重要性。
大衛活塞(00:57:46):
哦,我認為那是,是的,我認為絕對關鍵。我認為這是所有的,都是走廊上的對話,我想我在會議上做的另一件事是招人。就像我的大多數優秀博士後都來自那次會議。我認識的人不多,但肯定有很多都來自那次會議。你知道,你看到人們,你看到人們在做你感興趣的事情,然後問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如果他們是學生,然後你看到他們的博士導師就在拐角處,然後你得到了一份即時推薦信,然後你邀請他們吃晚餐,你可以隨意地和那個人交談,看看你想要在實驗室裏工作的人是否會給他們介紹一些實驗室裏的人讓實驗室裏的人過去。
彼得奧圖爾(00:58:34):
現在,你要讓我編輯那個a,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想被邀請,在下次BPS會議上和你共進晚餐。
大衛活塞(00:58:40):
彼得奧圖爾(00:58:42):
你還給我發了幾張照片我們的時間快到了。你能描述一下我們能看到的嗎?
大衛活塞(00:58:48):
噢,是的。這是,這是,這是我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所以我我以前經常唱歌。我的意思是,我仍然會唱一點,但在我50歲之後,我的聲音就不太好了。這是Nick Meegan,他是一個著名的指揮家,他是門德爾鬆的學者但是做了很多旋翼。我和他一起唱過幾次《彌賽亞》這是他在聖路易斯交響樂團的表演。他我不記得他那晚做了什麼。他那天晚上做了什麼,但後來我們為他舉行了招待會。我是聖路易斯交響樂團的董事會成員。 And so we had a reception for him. And so he’s my favorite conductor I’ve ever sang with. Uh we did, like I said, we did the Messiah with him and he’s, he’s said one of the, one of my favorite lines of conductor had ever said is there’s a, there’s a line in the Messiah, which is even so in Christ shall all be made alive. He sai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V in all of coral literature, cuz otherwise you say even so in Christ shall all be made a lie. And as a, as a singer, you know, working a lot with making sure your addiction is right. I thought that was very,
彼得奧圖爾(00:59:55):
那很好
大衛活塞(00:59:56):
一個。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我非常喜歡。我真的很喜歡。
彼得奧圖爾(00:59:58):
我不知道唱歌的事我很高興我提到了這張照片。是的。下一個。
大衛活塞(01:00:03):
是的。這是蘇魯。這是我的星際迷航,這是喬伊斯·賈卡。當時我在納什維爾交響樂團唱歌。我們做了Schonberg的作品華沙猶太區的幸存者。喬治是這個故事的敘述者。這是一篇非常有力量的文章作者藏在地下,他們把所有人都殺了,留下了他,但他活了下來。他聽到,他聽到所有猶太人被殺時,唱猶太歌。這就是它的意義所在。喬治是敘述者,他的家人,在二戰期間被關押在日本的拘留營中。 The Americans had set up and so it was really a, it was a great emotional night, but it was a, a, I wouldn’t say a fun piece to sing a very challenging piece and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never, it is the kind of thing you never, you can have a recording of it. It will never have a power of a, of a live performance of it. And so, yeah, I sang, sang with the Nashville symphony chorus for 23 years when I was at Vanderbilt and I sang, I sang professionally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mainly singing commercial jingles because I didn’t get paid very much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not that I was saying, I wanna remember to say,
彼得奧圖爾(01:01:30):
哦,正要說,你得給我們來首廣告歌。不,不,
大衛活塞(01:01:32):
不,不。我不打算,這是一個,一些,歌詞是,我們是第二大行業的第一。這還不是你需要知道的全部。
彼得奧圖爾(01:01:39):
大衛活塞(01:01:50):
我已經把這些都從我的記憶中抹去了。大多數都很糟糕。
彼得奧圖爾(01:01:54):
大衛活塞(01:02:01):
哦,這是緬因州。那是我的那是我在緬因州的小屋,住了20年當時我在緬因州教這門課。這是提醒我教導我的十字架。這就是魚的圖片。這是一間小屋裏。這意味著這裏不僅有一個生物實驗室。我每天,每年我都去那裏,拍一張這樣的照片。我想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天。天氣真好,很適合拍這樣的照片。
彼得奧圖爾(01:02:23):
但情況並不總是這樣。
大衛活塞(01:02:24):
不,不,不,不,不是真的。有一年全年都是水平降雨,這是這是同一個地方的日落。這是在MDIBL
彼得奧圖爾(01:02:32):
同一天,你又有了美好的一天。終於到了最後一個小時了我不敢相信我們已經到了最後一個小時。我們談到了社會的重要性,繼續。你研究的下一步是什麼?或者你能不說這些嗎?
大衛活塞(01:02:49):
哦,我的意思是,我們真的發現了這些,我們發現了幾種影響細胞胰高血糖素分泌的途徑。每個人都知道胰島素是一種來自於胰孔的激素,但是胰高血糖素是一種反調節激素當胰島素上升時,胰高血糖素下降,重要的是當胰島素當胰島素下降時,出現低血糖,胰高血糖素上升告訴肝髒然後製造更多的葡萄糖告訴你的身體釋放它,停止吸收它。在胰島素的存在下,胰高血糖素就不那麼重要了。它是一個很好的調節器,但在沒有胰島素的情況下,無論是在1型糖尿病中,當β細胞被殺死或在2型糖尿病中,胰島素失效,結果顯示胰高血糖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實際情況是,它並沒有下降,當它應該下降的時候,它卻上升了,這讓事情變得更糟。所以我們一直在研究通路。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麼在正常情況下調節它,或者,甚至在糖尿病中,但我們有一些我們認為可以調節它的途徑,不管它們是不是正常調節它的途徑在糖尿病情況下可以調節它。因此,我們正試圖篩選能夠擊中這些通路的藥物。我真的很想知道阿爾法細胞是如何工作的,但人們已經研究了45年了。我不認為我們比45年前更接近了。 So I, I don’t like to set goals that I’m probably not gonna reach, but I think we can actually have some potential drug targets that would be worth exploring for tr treatment of, especially if type one diabetes you know, at type two diabetes, I know how to treat just get some exercise. A lot of people get obese and don’t get type type two diabetes. And those tend to be, you can be very obese if you’re still moving a lot. You’re probably not so prone to getting diabetes. So it’s a disease not only of, of high caloric intake, whether it’s obesity or sugar or, but there’s also a, a, a sedentary component. And unfortunately, but that’s why we need more in person conferences. Cause you, you’re not sedentary at, in person conferences as much as you are at the zoom conferences.
彼得奧圖爾(01:05:04):
我正要問,那你是怎麼鍛煉身體的呢?
大衛活塞(01:05:08):
我是說這裏沒有電梯,所以我經常走樓梯。我,我走得很快。如果可以的話,我會騎自行車。不過我主要是騎健身自行車。秋天的時候我會看足球比賽,我會騎健身自行車,我看足球比賽的時候會騎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自行車,盡量在自行車上運動20英裏。因為我就像我說的,我可以,我可以,我喜歡看足球,但是是的,世界,世界。杯子總是好的。正確的。當你在看世界杯的時候,我的意思是,你一定在做別的事情。如果你在看足球
彼得奧圖爾(01:05:51):
是的。喝啤酒。
大衛活塞(01:05:53):
嗯,你也可以這麼做,但你可以在比賽的一半時間喝啤酒,然後騎健身自行車,在上半場,然後
彼得奧圖爾(01:05:59):
使
大衛活塞(01:05:59):
下半場請喝啤酒
彼得奧圖爾(01:06:00):
把下半部分的好東西都擦掉。戴夫,如果我們必須今天結束的話,因為現在已經到時間了。好的。非常感謝你們今天的到來。每一個人。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收聽,不要忘記訂閱。回去。在之前的幾集裏,Dave提到了很多技巧和技巧。戴夫,你能和一些非常棒的人交談真是太好了,我認為最後一點還有你要去哪裏,你是如何將你所有的物理知識運用到糖尿病研究中去的,我認為這非常好,這對很多觀眾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讓他們追隨你的熱情,追隨你的熱情,追隨你能成功的地方,追隨你感興趣的東西。
大衛活塞(01:06:39):
我隻想說做個科學家,而不是物理學家,化學家或生物學家。做個科學家就行了。
彼得奧圖爾(01:06:44):
這話說得真好,戴夫,非常感謝。
大衛活塞(01:06:48):
好的。拜拜
介紹/結尾部分(01:06:51):
感謝收聽由蔡司顯微鏡讚助的Bitesizebio播客The Microscopists,以查看本係列的所有音頻和視頻記錄,請訪問www.mobtapp.com/themicroscopist